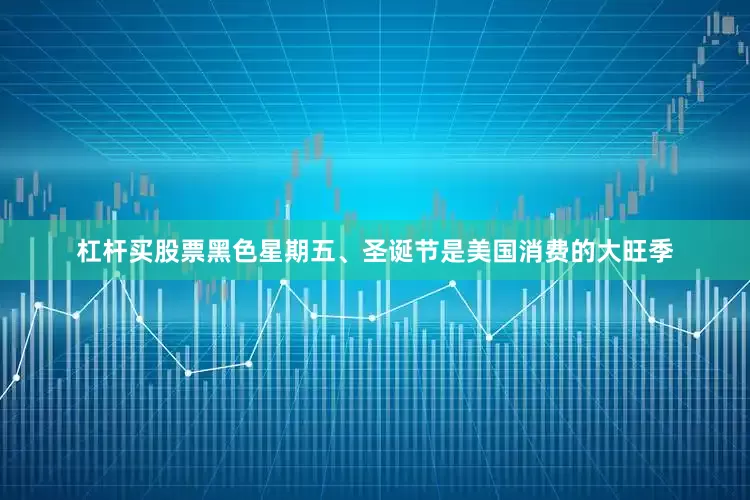在五代这个年代,脑袋离脖子有多远,远远没有今天保险。谁掌枪杆子,谁说了算。这不是段子,是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当年拍着桌子说的:“天子宁有种耶?兵强马壮者为之尔!”翻成白话,就是“谁拳头硬,谁就能当皇帝”。这话够直接,听起来像杀猪的吆喝,其实是千真万确的权力逻辑。
五代那个时代,讲究的不是祖宗基业,而是谁手里的刀快。
很多人一提“政权归属”,就爱把它说得神秘。其实在五代,皇帝就像大户人家养的狗,喂得不好,换一只也行。从李从珂、李丛厚到后来的军头,大家比的不是讲理,而是谁敢翻脸。李从珂的上位史,就是活生生的教材。

李从珂最早是李嗣源的义子,打过仗,吃过苦,立了不少功。结果,李嗣源还是信自己亲生的,皇位留给了性格柔弱的李丛厚。讲感情?和五代讲感情,等于和二手车贩子拼良心。李丛厚小子其实不算笨,他明白“兄弟如手足”,但为了皇位,手足也能剁。见李从珂这个义兄不服,就盯上他儿子李重吉,先拔了军权,想借李从珂奔丧的机会直接下黑手。对调职务、削权、调虎离山——套路一样不少。
可惜考倒了聪明反被聪明误,李从珂不动如山,就是不下河东。急了,就像请君入瓮请不到,李丛厚只能干看。等到李从珂举起“清君侧”的大旗起兵,其实兵力并不算强,结果被围在凤翔城。眼看就完蛋,他跑上城头大哭,说自己当年怎么和先帝同甘共苦。别小看这个哭,古代士兵心里比草地还软,一哭激起了风浪。督军张虔钊还不耐烦,非要硬攻,结果反把部下的火点着。

这下大家干脆造反,把李从珂推上了皇位。李从珂这个皇帝,是哭出来的。没有华丽仪式,也没有血统玄学,有的只是群情激愤和“干了他还有赏钱”的刺激。李从珂开价高:“打进洛阳,赏钱百缗!”大家也都明白,不是为祖宗江山,纯粹是分钱。“赏”字一出,士兵跟着拼命。李丛厚连累自己,逃到石敬瑭那,想找靠山,结果直接被石敬瑭给幽禁。历史证明,五代的信义,不如饭店的菜单靠谱。
李从珂顺利坐上皇帝交椅。可钱没发够,军头们马上就开始骂。像他这样被部下骂着讨要工资的皇帝,古今少见。不是他能赖账,实在是地方上早已破败,国库空虚。不给钱,等着被推翻就是了。这种权力循环,比风扇都快。一茬接一茬的皇帝,都像雇来的经理人,谁能养住一群大爷式军头,谁就多呆一天。

五代最经典的主题就是:当皇帝还不如做军头踏实。
别说大人,幼主更是没戏。赵匡胤就是在柴家幼子的名义下夺的位。湖南割据的武平政权也一样,周保权才十岁,张文表直接翻脸。这种前车之鉴,谁见了不发愁?赵匡胤起初也是这么上来的,知道这游戏没规则,所以上位后生怕历史在自己儿子身上重演。
赵匡胤初登基,儿子都还小,外有割据军阀,内有老資格、手握兵权的军头。别说自己能不能善终,就算宋朝能不能传到第二代都是未知数。要是效仿前面那些强行推未成年儿子上位,局势不稳,朝中军头一个个都像看笑话一样围着等机会。
所以赵匡胤最开始就不是非要儿子继位。怕儿子年幼撑不住场面,还不如让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弟弟赵光义来顶上。大家一条线,没人敢乱动,江山还是老赵家的。

于是,隐储制度就成了宋朝开国的“冷门科技树”。明面上不立太子,但背地里什么亲王、京尹、都城控制权,赵光义通通拿下。别人豢养亲兵是祸心,自己弟弟豢养亲兵是安排。赵匡胤对赵光义的宠爱,那可是恨不得把家底都交给他。
但,这事就跟买保险分红一样,保险到期钱还没见着,局势突然变了。天下一统,儿子们也一个个长大了。继续让弟弟压着不合理,可儿子没有培养起来,再换人又来不及。这种接力棒的迷局,换成谁都掉头发。
再说,五代能正常当太子的都少。立了太子,东宫就是另一个小皇帝,不折腾一番才怪。太子们不愿意进东宫,说白了就是怕被软禁、失去兵权,名头响其实是个“闲人”。

在这个体制里,谁敢明着立太子,等着人事内斗就好。皇帝怕太子谋反,太子怕被当摆设。所谓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,基本是史官写在纸上的,现实里连纸都懒得糊墙。
于是五代主流继承方式变成了“谁拳头大,谁说了算,名分啥的都不重要”。隐皇储这个方案恰好满足所有人的心思:不公开,不高调,但该给的权力给足。
到了开宝六年,赵光义被封王,算是站到了幕后主角的位置。开封尹是首都老大,京师里谁都得听。和他同一级别的兄弟,只有他有王爵,这就不是一般的暗示,而是明牌了。
但你以为赵匡胤能顺利交棒?想得美。俗话说水往低处流,权力往高处攀。赵匡胤晚年,突然讲起了“迁都”。平常风平浪静,突然要迁都洛阳。政坛老狐狸们都知道,想换根本不是地理,更不是风水,是要削弱赵光义在开封的根基,给新接班人腾地儿。

赵光义一看,自己经营多年的开封要拱手让人,当然不同意。兄弟两人第一次正面杠上,赵匡胤还赌气要迁都长安,显然不是真的要迁,都说迁都背后是换储君的算盘。
这边培养赵光义,那边又捧三弟赵廷美,对外联合名将、对内培养心腹。用摧毁南唐的大功劳,来壮大家族势力。对比一下,连小儿子赵德昭也开始出来露面,参加大政活动。谁都明白,这局越下越复杂。
可兄弟互掐,外部势力也来掺和。赵光义拉拢韩重赟、王审琦,联姻关系网满天飞。赵匡胤察觉后,随手换掉史珪,给赵德芳安排岳父,让其治理洛阳,修宫殿,一看就知道是为迁都搭台子。可一旦迁都,开封权贵、禁军家属得全部搬家,利益触动太大。权贵的土地人口一调查,损失不能接受。这不是简单的首都挪窝,是彻底洗牌。

连赵廷美自己都明白,老哥捧自己无非是用来制衡二哥。至于真心让自己当皇帝,信他不如信牛下崽。在这种多方权力博弈下,赵匡胤终于放弃了迁都的念头。
你看来,这是赵匡胤一生的心病:权力到底传给自己那一脉,还是护住整个赵家?
从隐储到明储,从推三弟到扶儿子,赵匡胤进退两难。他自己也不长寿。家族里长寿基因不强,他能不能再活几年都是未知数。保守点,维稳最重要。
最后赵匡胤突然暴亡,赵光义顺理成章继位。说到“烛影斧声”,其实是百年后宋人文莹的一句野语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都点评:“然观其始末,并无指斥逆节之事,特后人误会其词,致生疑窦。”这么说,这事纯属传说。

我们换个思路,赵匡胤临终夜,可能真的叫弟弟喝酒,交待后事。要是非说赵光义谋害亲哥,也难免对后来的政策看走眼。
但无论如何,赵匡胤死后,赵光义把五代的老本行彻底掐死,强行把传承规则拽回“父子相传”的传统路线上。《烛影斧声》的戏说,不过是大家对权力游戏的惯性怀疑。 归根到底,是五代那套“枪杆子选天子”的模式玩不转了,江山基业才回归到“谁能护家业,谁为传人”。
这一圈折腾下来,皇帝变军头,军头变皇帝,到头来还是要找个归宿。说到底,权力这东西,靠哭、靠打、靠兄弟义气都能拿到手,唯独靠不了一成不变的规矩。
这桩事没有终极答案。放到今天职场,说不定你也能看到:老板找接班人,找儿子,找兄弟,最后看谁能护住摊子。五代的江湖,虽远犹近。

想到这里,也忍不住琢磨一句:你如果是赵匡胤,手抓着传国玉玺,翻来覆去该交给谁,舍得吗? 归根到底——世道风云,权柄传人,还是那句老话:没有永远的王朝,只有讲究的分寸。
九八策略-股票配资平台门户官网-普通人怎么加杠杆买股票-股票配资保证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